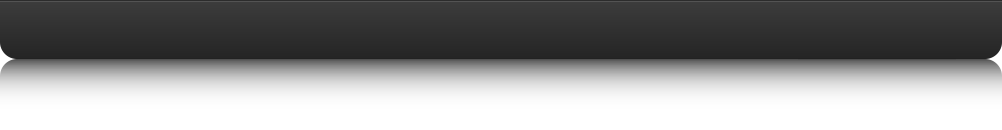就北宋初期而言,家族伦理是指以“敬宗收族”为核心的祭祀、家训、族规等内容。“敬宗收族”一词出自《礼记?大传》,“亲亲故尊祖,尊祖故敬宗,敬宗故收族,收族故宗庙严,宗庙严故重社稷,重社稷故爱百姓。爱百姓故刑罚中,刑罚中故庶民安,庶民安故财用足,财用足故百志成,百志成故礼俗刑,礼俗刑然后乐”。从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,敬宗的目的是收族,故曰“敬宗收族”,敬宗收族所体现出的作用即“礼俗刑然后乐”,以礼俗取代刑法,而百姓安乐,社稷稳固。这实际上是最早的文化控制思想了。唐代,这种社会控制思想进一步发展,“祭祀之有尸也,宗庙之主也,示民有事也。修宗庙,敬祀事,教民追孝也”。至宋初时,随着血缘家庭的肢解,族内地位的日趋平等,社会上宗族成员关系松散。加之商品经济的冲击,经常会使得富者有社会地位不稳之虞,贫者有失去生存能力之忧,这种状况,既不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,亦损害了新兴的士人的存续和发展。因此,宋代的士人阶层祭出了“敬宗收族”的旗号,此时敬宗收族的作用,诚如欧阳修所言,是在“五代之际,礼乐崩坏,三纲五常之道绝”的情况下,为了实现“经国家,定社棱,序民人,利后嗣”的目的而来。士人阶层力图重新振兴宗族, 利用宗族这个古老的自然共同体,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,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。随着士人家族的正式出现。宗族的社会职能由阶级分层(选官、婚配),一改而为“敬宗收族”。湖北热气球租赁
虽然,“敬宗收族”的目的在于收族,但“敬宗”却是达到“收族”的最佳方式,以敬宗之名而行收族之实,进而达到稳定整个家族的目的。但在宋初,即便是士大夫之家亦是“耳目久不际,往往不知庙之可设于家也”。因此,在宋仁宗庆历元年(1041)“听文武官依旧式立家庙”之前,宋初的家族祭祀是“士庶皆祭于寝”的形式,称之为“寝祭”,即祭祖的场所亦是日常生活之地,将人神置于同一处,显得非常的随意,很不庄重,是对祖先神灵的不尊敬。因此,其祭祀规模和产生的影响都非常有限,虽有敬宗之意,但收族之效却不明显。因此一些有见识士人依据自己家族的具体情况,创立祠堂祭祀祖先的方式,真宗咸平年间,任载之子康懿公任中正建祠奉其先祖,曰“家祠堂”,祠堂内神主之位皆依尊卑长幼之序摆放,“其严慈之尊,长幼之序,煌煌遗像,堂堂如生。宗属以之视瞻,精爽以之冯附。”任氏以庄严肃穆的祠堂代替出入随意的居所,行祭祖之事,以此来感召族众,使得众人皆心向族内“精爽以冯附”,并且以“严慈之尊”、“长幼有序”大大增强了家族的凝聚力。更重要的是任氏祠堂一反“前代私庙并置京师”的方式,“而复设于居里”,将祠堂固定在家族所在地,既便于族人瞻仰祭祀先祖,又能通过家族祭祀来团聚族众,从而达到“收族”的目的。
同样设立专门场所祭祀家族祖先的还有被称为“宋初三先生”之一的石介,庆历元年(1041)十一月二十日,宋仁宗南郊赦书“听文武官依旧式立家庙”,而就在同一年稍早的八月八日,石介已然“缘古礼而出新意”,“自为之制”,“于宅东北位作堂三楹”,名之曰“祭堂”,“举大王父以下为三十二坟,葬于祖莹,复立祭堂于宅东北位。葬之以礼,祭之以礼也”。待到宋中期家庙宗祠更是日益繁盛,其宗旨亦上升到“经国家,定社稷,序民人,利后嗣”的高度。可见,从宋初开始,士大夫家族就充分认识到家族祭祀强化祖先认同、明确尊卑长幼之序,从而强化对族众控制的功效。“收族者,谓别亲疎(疏),序昭穆”,在敬宗过程中建立祠堂,祭祀家族祖先,其目的在于将族人全部纳入家族内部的伦理体系,使得族众具有团结意识,相互帮助、和睦相处。范仲淹曾说:“吾吴中宗族甚众,于吾固有亲疏,然以吾祖宗视之,则均是子孙,固无亲疏也。”同宗共祖的血脉亲情成为强化族人凝聚力的必要手段。
但是,仅仅依靠祭祀祖先的仪式形成权威,对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进行日常管理,是非常不现实的,由此,更便于实际操作的家训、族规的提出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宋初大多数家训、族规皆以和睦家庭、巩固家族为宗旨,于家族中弘扬“孝悌”观念。以宋初宰相第一人范质的《戒从子诗》为例,“戒尔学立身,莫若先孝弟,怡怡奉亲长,不敢生骄易,战战复兢兢,造次必于是”。范质将孝悌作为后世子弟为人处世的首要准则,并将之看作延续家门的不二法门。其后的宋祁亦在《庭诫》中总结道:“要举一孝百行阁不该焉”,“人性苟有一孝,则无所不包,犹树根一固,而百枝生焉”,孝悌成为家训首诫,所谓百善孝为先,作为家族一员,无论功绩操守如何,一旦被认为是不孝之人,就将成为“名教”罪人,为人所不齿。而家训亦是通过孝顺父母,和睦兄弟,维护“孝悌之道”,达到家庭和睦之目的,进而孝悌及于家族,使家族和睦,并在此基础上维持聚居大家族的稳定。
在家训的基础上,对于家族更加有约束力的家法、族规也日益成熟。以宋初名相李昉家族为例,李昉之后四子,宗讷、宗诲、宗谔、宗谅均入朝为官,其家族亦成为宋初声名最隆的家族。但是作为一个“子孙数世,二百余,犹同居共爨”的大家族,其家族的维持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使得李昉家族经久不衰的正是其严谨周详的家法,时人皆称李氏家族“门内之治有规,田园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禄,皆聚之一库,计口日给饼饭,婚姻丧葬所费,皆有常数。分命子弟掌其事”,其家财产共有,按例统一分派,族众自然归聚到门下。除此之外,李氏家族尤其重视尊卑长幼的身份等级的管理,即便是“憧憧往来,盈门交道”,亦“亲疏有序,荣瘁不移,子妇佐馔,儿童捧觞”,足见其家法等级之严明。同时,李昉亦以忠孝家风传家,以儒学教育兴门户,李昉曾经教育子弟“尔等各勉强学问,思所以起家,为忠孝以立身”,家传儒学既有科举及第的功效,又与忠孝家风相辅相成,其族中子弟多能“清素谨孝”,以至于宋真宗对李昉三子李宗谔说:“闻卿至孝,宗族颇多,长幼雍睦。朕嗣守二圣基业,亦如卿之保守门户也”,而李氏家族子弟亦没有让世人失望,有宋一朝其族中科举及第者一十五人之多,这对于李氏家族的传承和社会地位的维持是有力的保障。 实际上,以祠堂祭祀和家训、族规为代表的家族控制方式对基层社会文化控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,但是,必须清楚的一点是,基层社会文化控制与专制王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。所谓家法、族规虽意在维系一家、一族的繁荣昌盛,但随着士人的重视,以及印刷技术的发展,使得各类的家训、族规广泛的流传于社会之中。如后世袁采著名的《袁氏世范》,其文言浅意深,辅以日常范例,即便不曾读书识字的人,亦可明白其旨意,淳熙戊戌成书之后即刻板印刷,因而在基层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。不仅如此,宋代几部重要的家训成为私塾、族学教材,如吕本中的《童蒙训》即“是书其家塾训课之本也”。此时的祭祀、家训、族规已经由“立身”、“存家”一改而为“厚人伦,而美习俗”,甚至达到了“可以行之一时,垂之后世可也”xxii的高度,成为当之无愧的“世范”。赵宋朝廷之所以倡导、推崇宗族文化,甚至在国家法典中将一些有关祠堂祭祀与族规的事务加以强制规定,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。这样,宗族这一一度受到冲击的自然共同体,又在宗族伦理文化的作用下重新具备了约束族众的功能,并在士人的大力倡导之下由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社会领域,并且深入基层日常生活,在维护家庭乃至于家族的努力过程中,宗族伦理文化取代了强制的人身关系。文化控制也就成为维护宗族的主要手段,并进一步的延伸到整个基层社会的控制上,进而成为专制王朝社会控制的工具,达到“结之不以恩惠,威之不以刑罚,不为而治”的效果,从而进一步稳定了基层社会,维护了赵宋王朝的统治。